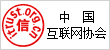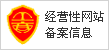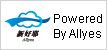酒如泉,剑如虹
清代张潮说:“因雪想高士,因花想美人,因酒想侠客,因月想好友,因山水想得意诗文。”看来,不同的情景、物状会引起人的不同联想。事实上,侠客确实好酒,侠无酒不显其壮,酒无侠不显其烈,侠客与酒结缘,实出于其内在的必然。
侠客之好酒,与普通酒徒之嗜酒相较,其高下之分,判若云泥。在侠客那里,酒绝不仅仅是佐餐之物,而是生命的滋养品。侠有酒的滋养,才得以剑气纵横;酒入侠肠,酒才具备了生命形态。侠与酒,在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其文化品格上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。
侠客是游离于俗常规范外的一群,他们摆脱了陈腐的观念,恣意挥洒着个体生命情感。对功名,他们是“深藏功与名”,对利禄,他们“不羡山河赏”,对家庭重负,他们也甚至表示“安能对儿女,垂帷弄笔墨”,至于对待死亡,只要有“侠骨香”,纵死千次也在所不惜。因此,酒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“身外之物”。他们因酒而更自由,因自由而得以更多地发挥生命的潜能,把酒当作生命的催化剂,以破樊篱、冲罗网,以彰显生存实相。酒之于侠,犹风之于火,以隐以显,以长以消,侠之好酒,乃在于其内在精神的相通。
“笑尽一杯酒,杀人都市中”,是侠客的潇洒;“失意杯酒间,白刃起相仇”是侠客的意气;“荆轲饮燕市,酒酣气益振”,是侠客的豪迈;“片心惆怅清平世,酒市无人问布衣”,是侠客的失意;“落花踏尽游何处,笑入胡姬酒肆中”,是侠客的多情。“英雄侠骨美人心”,无不需要借酒彰显,侠也就恢复了自然真实的本来面目。金庸小说里的侠客,亦复如此。《天龙八部》里的萧峰,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洪七公,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令狐冲等,莫不好酒,这些人可亲可敬可怜可爱,恰是侠客之正格。至于郭靖、段皇爷等人,端正肃穆,拘于礼俗,俨然是民族功臣、精神导师,其不好酒,亦在必然。
酒之为德,正与侠客的生命情调通。刘伶《酒德颂》云:“……兀然而醉,豁然而醒,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孰视不睹泰山之形。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。”天地万物,俗常规范,尽皆烟消云散,唯有个体生命的体验才是内在的真实。不仅如此,酒甚至可以使时光错置、年岁倒流,陆游诗云:“酒酣霞晕力通神,淡淡鹅雏色可人。一笑破除垂老日,满怀摇荡隔年春”。至于李白说“三杯通大道,五斗合自然”,苏轼说“杳冥冥其似道,径得天真”,那直是说欲体验本真生命,唯须饮酒了。
把酒当作通向本真生命的媒介,中西皆然。中国有刘伶之“酒德”,西哲有尼采之“酒神”。在尼采看来,酒神象征情绪放纵,在痛苦与狂欢交织的颠狂状态中撕去外观幻觉,直视人生悲剧,以体验悲剧来重新肯定人生,并认为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。中国的诗人饮酒、侠客好酒,概具“酒神精神”。自刘伶《酒德颂》以下,酒与艺术愈更加密不可解。杜甫作《酒中八仙歌》,使人惊诧于诗、书、画与酒的关系,至于以酒消解悲剧意识,更是蔚为传统。更有趣的是酒隐,孟郊有“彼隐山万曲,我隐酒一杯”,苏轼有《酒隐赋》,隐逸出世不必远避人间,只须寄情于“壶中天地”。酒之妙用,至此可尽矣。
但最具中国特色的,当是侠客之好酒。侠客本就“不轨于正义”,陈规陋俗也就无须刻意消解,这就比文人少了一层顾忌,只须痛饮美酒,恣意行侠,也就通大道、返自然了。尽情挥酒着天赋本真,在面对悲剧真相中体验到超越的快乐,这就是侠客的艺术人生。在文人那里,酒还可能成为一剂麻醉药,使人沉迷萎缩,但在侠客那里,酒却只能使人的生命得以张扬,酒的文化内涵也才能发挥到极致,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形式。
酒不仅与侠客有关,在中国历史上,酒甚至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有着密切的联系。《战国策》云:“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,进之禹,禹饮而甘之,遂疏仪狄,绝旨酒。曰:‘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’。”《韩非子》也有记载,说齐桓公酒醉失态,丢了帽子,深以为耻,急忙行善政改变自己的形象。在没有民主的集权时代,君主的个人品德及其才具往往对国家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是以清醒的君王无不对酒深自戒之。酒之为用可谓大矣!
只是自仪狄、杜康作酒,延而至今,酒风大盛而又酒德大衰。在古人那里,上焉者把酒当作生命的滋养品,下焉者借酒自沉,至不济也当作佐餐之物。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,以上诸种均不足为训,酒在他们那里蜕变成了一块无形的遮羞布,借酒盖脸,道无耻之言,逞卑鄙之行,置道德公益于不顾,坑国害民,他们似醉实醒,无非是为了实现一己之私欲。酒德不振,一衰至此,先圣有知,甚恐要对做酒的功过重新评定了。
酒与侠的结缘,正得其所,酒德不振与侠风的消歇也正同步而行。酒可使人张扬个性,亦可使人沉溺乃至卑微;酒可祸乱国家,亦可振作民族精神。酒无定性,唯人所使,若在酒怀中倾满大侠精神,那就千杯嫌少了!
酒如泉,剑如虹。饮酒的超脱替代不了现实,长剑虽利终不能尽除妖孽。但只要有这份精神在,终不至灭绝了正义与天真的希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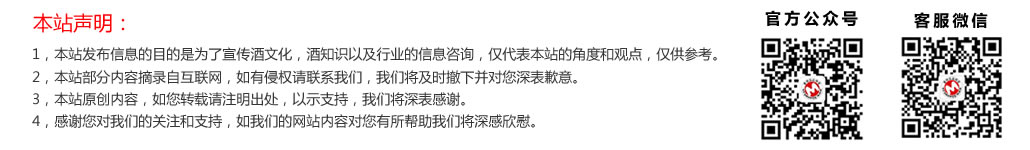 |
| 上一篇: 白酒文化需向下,向下,再向下! |
| 下一篇: “同宗同脉”的荣耀 |
- 相关资讯
- 推荐阅读
- 热点资讯
- 5月12日茅台及系列酒,部分名酒行情价格2021/05/14
- 杨陵江回应酒业份额论:明年1919加阿里酒水…2018/11/23
- 王朝酒业没落:业绩连年巨亏,解百纳甜蜜素不合…2018/11/23
- 白酒专家:星河湾老原酒“中华一绝”2015/03/20
- 梁起建:一个年轻农民的“葡萄梦”2014/07/26
- 5月12日茅台及系列酒,部分名酒行情价格2021/05/14
- 走进世界上最出名的5种加强型葡萄酒2013/12/02
- 最令人费解的10张葡萄酒酒标2013/12/02
- 最令人费解的10张葡萄酒酒标2013/12/02
- 汇丰酒厂金瓜长寿酒瓶里长金瓜2014/04/02
- 走进世界上最出名的5种加强型葡萄酒2013/12/02
- 茅台集团副总张德芹:茅台当不当国酒不重要2014/06/07
- 姚明葡萄酒受到业界的到肯定2014/06/05
猜你喜欢
- 限量版红酒让嘉宾流连2014/06/03
- 茅台袁仁国谈白酒行业要仰望星空:…2014/06/07
- 中国企业为何大而不强2013/08/21
- 品鉴进口酒不再进“雾区”2014/03/11
- 武汉女白领KTV里连飙高音 唱破…2014/05/15
- 酒参展,瓶瓶盖盖跟到来2014/03/24
- 不摆酒返礼金是钻“禁酒令”空子2014/03/14
- 全球最著名的十大“奇葩”葡萄酒2016/11/26
- 食品安全宣传周酒类知识公益宣传活…2014/07/20
- 共享世界杯激情董酒邀你猜冠军2014/05/27 >